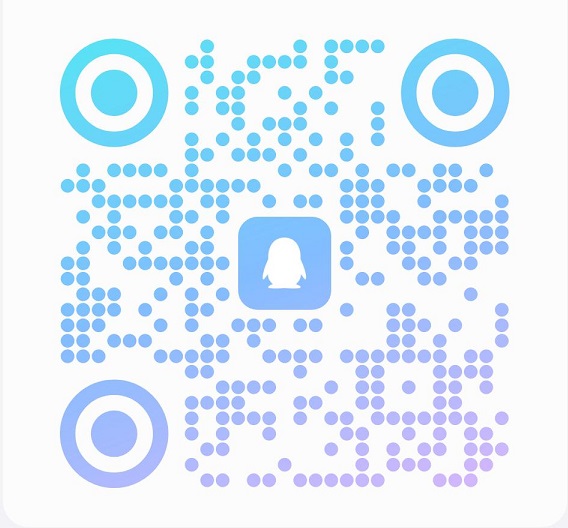二零零九年的《母亲》不仅在时代上生不逢时,在内容上更是太过不正确,政治意义上的不正确。谈论「母亲」的角色,若能温馨地呈现,即便科幻只是一种手法,然而只要符合政治上的「东方(oriental)」想像,或许就会像《妈的多重宇宙》一样获奖、赞誉无数。

「为母则强」、「养儿方知父母恩」、「天下父母心」作为谚语,道尽父母在华人文化中所具有的角色特质,而这特质无不来自儒家五伦之一的亲子关系。伦常在这种文化体系下,是如同法律一般的规范,换言之,身分关系的固定也决定了其间的行为准则,也将基于身分关系的所有作为给正当化。
“Mother” 不只是片名,也是主角的名字,更是故事的主轴。不知原因的父亲缺席,让母亲与智能障碍的儿子尹斗俊构成这个家庭中的唯二单位。已届成年的尹斗俊的唯一朋友是镇泰,但从电影开始时带着尹斗俊去报仇,踹掉肇事逃逸黑色宾士的后照镜就可知道镇泰是个说不上善良的流氓。
智能障碍并不阻碍成年身躯的性,类似的议题在李沧东的《绿洲》已有特别探讨。同样的,在《骨》中的尹斗俊在某日酒后返家路途上,一时兴起跟踪女高中生文雅婷到废屋提出性邀约,想当然的是被拒绝。然而,隔日该女高中生就已倒挂在废屋度高台上,头部有被钝器重击的迹象并呈现死亡,而那里,是一个全村都看得见的高台。
作为最后被看见行踪的村民,尹斗俊被当作重大嫌疑人逮捕,甚至在讯问室被以特殊的方式逼供(其中一名刑警要被讯问人尹斗俊咬住苹果,再以踢击的方式削去苹果外露的半侧),但同时也再三提醒尹斗俊对于讯问笔录所记载的犯罪事实要确认后才能签名。
经由画面所揭露出的刑求,以及故事中提示媒体亦如此报导,理所当然地我们就能怀疑这份自白的任意性—亦即对于犯罪事实为承认的陈述是否可信的关键判准。当然,爱子至极的尹斗俊母亲也正当地如此怀疑。
于是他跟踪办案刑警帝文到车上试图拿中药材贿赂,未果后再跟踪尹斗俊那唯一的朋友镇泰,毕竟是流氓,做出这种杀害他人的事也是合情合理。侵入住居后果然在镇泰的衣柜中发现了一支沾有红色液体痕迹的高尔夫球杆,电影再度提示给作为观者的我们一丝希望,毕竟智能障碍者的无知—innocence—无辜甚至是如同常识一般的前提。只不过这只是另一次碰壁,那个红色液体痕迹不过是镇泰女伴留下的口红印。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为何会以「母亲」为名,在母爱的光环下,愿意四周奔波,做起了调查机关该做的工作,甚至涉险搜集证据。更不用说找镇泰把知道消息的两个高中男生「取证(痛打一顿)」—这里也能呼应警察对于斗俊的「取证」方式,原来高中女生文雅婷是个援交少女,并且手机拍下了每个恩客的照片。那么根据在这个故时刻所具有的资料所能作出的合理推估,即凶手是这几十张照片中的一人,同时,尹斗俊又想起了那晚所见在废屋中有个老人,这个老人恰好又是在母亲探监提示手机照片时档案库的其中一张肖像。
母亲以中医团体的名义拜访了这位老人,正好与其自身所从事的密医针灸相关。老人说虽然身体最近没有不适,但心脏不太舒服,理由因为前阵子村内所发生的杀人案件,他看到了不该看的事。以拾荒为业的他,有时会到那间废屋去过夜,事发那晚恰巧如此。他看到了尾随着文雅婷的尹斗俊,尹斗俊问了:「妳不喜欢男人?」被一路跟随的文雅婷感到不耐,向外丢了颗大石头作威吓状,并回答说:「我讨厌男人,所以少在随便胡说八道你这笨蛋。」
这时,尹斗俊把大石头丢向文雅婷,砸到她的头顶。
关键字是:「笨蛋」。在故事的前段,尹斗俊在狱中曾努力回想案发当晚时被狱友戏闹而打了一架,尹斗俊母亲看了他的伤势忍不住碎念道为什么要打架,不解的母亲却听到儿子这样回答:
「妳不是说只要有人看不起我,就要踹对方一脚吗?」
「没错,要是有人看不起你的话…」
「就要踹对方一脚。」
「只要有人打你一下…」
「就要打两下回去。」
在剧情的层层误导中,作为观者的我们以为凶手不是天真的智能障碍者,而是他身旁想栽赃给他的流氓朋友;我们以为凶手是想把杀人成果暴露给全村看的变态,没想到却是不小心发生意外想要求救的讯号;我们以为凶手是被害少女援交联盟的成员之一,结果该人却是目击者;我们再以为凶手是那位拾荒老人所看到的尚未出现于故事中的人物。至此,我们仍在否认着尹斗俊作为凶手的可能。
故事到这里全盘推翻所有情节所能得出的「合理推论」,反而在一个强烈的人物设定之下扭转了整个剧情,也就是:「母亲」。
充满母爱的母亲对于智能障碍儿子的谆谆教诲是为了不让爱子被欺负,但正因智能不足无法思考规则的适用范围,使得规则成为教条,只要有任何对自己的不当对待,就必然要「过度反击」。这样的反应如同条件反射,亦即,没有足够思考能力的智能障碍者尹斗俊面对世界的刺激所能给出的回应,就如同敲击膝盖的反弹一般。
同时,《骨》也具有韩国电影所具有的特征,道德上的善恶(西方的、基督教价值标准下的)并不被当作普世准则对待,也就是说这样的电影文本也没有正反派可言。我们会发现即便一方是错的,不再能径自推论另一方就是对的,或是,有人做了错事,但此等作为却又如此情有可原。涵摄到《骨》的故事中也就是,警察固然有刑求,但也确实抓到了人犯;尹斗俊确实杀了人,但也不真正地具有杀意。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不再有确切的行为准则可以依循。
然而,凶手的现身并不是故事的结束,故事的主角已经其实早就被开门见山地揭露在片名:《Mother》。为了保护儿子,把唯一的目击者拾荒老人给灭口是必要的手段,而(尹斗俊的)母亲也确实这么做了,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地将该老人的住居处也一并焚毁。死无对证的情况下,纵使具有一份自白也不足以为证,故事中顺理成章地由刑警帝文宣称破案,他们抓到了「真正的凶手」,是一位在祈祷院名叫宗八的男子,当然地尹斗俊也就获释。 (尹斗俊的)母亲选择去看这位凶手,毕竟她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惟当她发现宗八也是智能障碍者,甚至连双亲(母亲)都没有时,却溃堤了。
故事的最后是恢复正常的日子,我们看到画面上的母亲坐上了老人出游的专车,众人在车上歌舞时原先坐着的她拿起细针,灸了一个在大腿的穴道,关于这个穴道她说过:「有个穴位,可以帮助你忘却一切可怕的坏事,跟解开所有心结。」,看来似乎奏效了,(尹斗俊的)母亲走向了欢乐的人群,一同共舞。
故事中的所有角色都有姓名,唯独尹斗俊的母亲却是无名的,只有「母亲」这个名字—身分。她看来十分朴素,就像我们对母亲所具有的想像一样,那种携子长大所不得不成为的人老珠黄、打扮从简、不顾美丑只重实用。对儿子的保护正好是「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个古谚的呈现,不仅教导反击一定要过度,甚至是只要自家人不要出事其他一切都无关,于是我们能看见那种「都是别人教坏我的小孩」类型的长辈到底是怎么样的面貌。
高中女生文雅婷的死最后所揭露的真凶固然是尹斗俊,然而如同前述刑警亦非使用合法的手段取证,充其量这种巧合只不过是误打误撞的好运。偏偏「好运」并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检警侦查机关所该依凭的,于是故事的最后再度点醒了我们草率行事的刑事终究不过是以偶然却非科学来办案,那么谁是凶手这个兹事体大的问题竟然只是一个运气问题。 (尹斗俊的)母亲会见了被当作替罪羊的宗八,不仅是她深知凶手并不是他而为其抱屈而泣,更是因为宗八与尹斗俊相同都是智能障碍者,更难让她不将宗八的处境投射于尹斗俊身上。毕竟,如果她是他的母亲的话,她也会不顾一切地保护孩子,为了孩子赴汤蹈火、杀人灭口,在所不惜,不是吗?
(尹斗俊的)母亲为宗八掉下的眼泪,是因于他的无母,而不是他被冤枉的无辜。
刺进那个穴道,忘解一切烦忧。未来能回到尹斗俊与母亲都没有这段恶梦般记忆的生活,但我们也能猜想或许母亲消去了尹斗俊的所有不好记忆,只为了让他快乐,甚至,让他一直保持在幼稚状态(或许智能不足是母亲持续消去其记忆所致),让自己能继续当个「母亲」。特别是,记忆消除的个体,自我将不再具有连续性,也就不再具有同一性,自己不再是自己,也就难以令不同的自己为了另一个—过去的自己所做出的事—犯下的罪负起责任。
我们太熟悉了,一个为了孩子好、出于爱的行动、以母爱之名,可以实现各种不可能奇迹的母亲。她能创造生命,也能夺去生命。为了你好,于是不让你跟那些朋友来往;为了你好,于是不让你自由恋爱;为了你好,所以不让你选择所欲;为了你好,所以带你烧炭自杀;为了你好,所以谋杀会让你陷于不利的其他人。即便,其他人也有爱着他们的母亲,然而,这一切只因为母亲爱你。
啊,母亲的孩子。
母爱,正因此而伟大。
又名:骨肉同谋 / 非常母亲